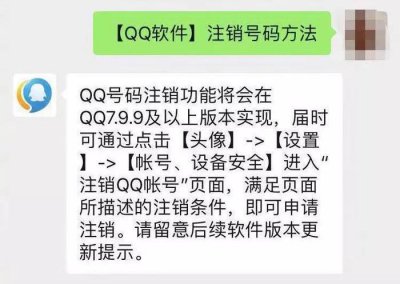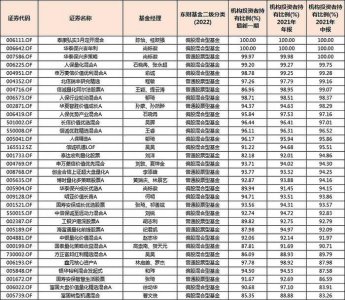林亿:为了写我想写的音乐,来到中国
人为什么要迁徙,从一个国家抵达另一种文明,去适应一套崭新的语言、思维和行为体系?在南海之声《听见》栏目的专访中,我们试图从新加坡音乐人林亿的身上寻找答案。
林亿是新加坡第六代华人,是在新加坡双语政策下成长起来的一代,英语是主要沟通和思维语言。2013年他来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攻读作曲系硕士,在彼时的新加坡,去语言相通、音乐教育体系相似的欧美国家就读,是大多数人的选择。因为少时在校民乐团学习“笙”这个中国的古老乐器,并且渴望在民乐上有更深的建树,林亿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。如今十年已过,完成学业后的林亿,一切是否如他当年的期冀呢?在外人看来,林亿的选择无疑是成功的,如今他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工作室,为《理想照耀中国》《创业时代》等影视剧配乐,作品有着不错的口碑;在生活上,他与中国青年琵琶演奏家孙莹因乐生情,组建了跨国家庭,也拥有了事业上的好搭档。
林亿本人如何看待这十年的迁徙经历和此时的人生,我们又能从他的视角看到什么样的中国?

选择
“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,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以英语为主的社会。在学校,所有学生都学习英文,英语成了我们社会的主导语言。”
——选自《李光耀回忆录:我一生的挑战——新加坡双语之路》
《听见》:2013年来到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攻读作曲系硕士,这是个艰难的选择么?
林亿:我的第一个想法是跟新加坡国人一样,深造读硕士肯定是去欧美国家。当时我的阿姨定居在美国洛杉矶,所以我一直准备考洛杉矶的两家音乐学校。其实我是在最后时刻才有所转心,去洛杉矶的选择太简单了,而且课程是一年的时间,没法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造,尤其是中国民乐的创作上。当时我已经给新加坡华人团写了几个作品,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很自信,最后时刻我才决定来中国,在民乐上有所深造。
《听见》:来中国求学,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?
林亿:那时候我的中文比现在还要糟糕至少100倍,说不出一句流畅的话。尽管入学考试的很多内容已经学习过,但是需要重新用中文学习这些专业知识,脑子里需要不停地翻译。
《听见》:身边的朋友,怎么看待你当时的选择?
林亿:虽然自己很坚决,但是确实周边没有一个人赞同或者鼓励这个决定。当年我过来的时候,中国在大部分新加坡人印象里,还停留在那种六七十年代,张艺谋老电影的感觉。甚至还有同事问我:你又去北京了,北京有没有厕所,听到这些我就都不想接话了。

缘起
在新加坡,教育部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,注重学术学习能力之外的培养。每位学生在校期间都被要求加入一个艺术团体,作为“课外活动”计入分数。1998年末,初三学生林亿加入了学校里比较小众的民乐团,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传统乐器“笙”。
《听见》:在新加坡,人们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学习民乐?你是怎么接触到“笙”这个乐器的?
林亿:新加坡学习华乐的方式跟中国有点不一样,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。中国的孩子从小拜师入门,然后一对一地跟一位老师学习某个乐器。我们那边一般是通过学校的课外活动,加入一个艺术团体,然后直接学习乐队的曲子。
我所在的学校是一间英校,有一支民乐团的存在也是比较意外的事情,因此招新很困难。有一次老师又来找乐手,他说我是田径队的,肺活量肯定特别好,应该去。那天我正好没有别的课外活动,就跟着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“笙”这个乐器,看起来特别高科技,很像机械枪,就觉得好酷,还挺有意思的。我是属于任何事只要下定决心,就一定要很用心地把它完成,学笙也是这样,就一路学了下来。

《听见》:大学本科你学习音乐专业,但并不是走上演奏的这条路,而是选取了作曲的方向,为什么?
林亿:一直以来我坐在大乐团里演奏,除了我自己该演奏的部分,我的大脑一直在飘,一直在听别的乐器在演奏的声部。每次大乐队排练结束后,我很喜欢到指挥台那边去看总谱,很想知道别人在做什么,为什么他跟我不一样,或者他跟我一样,然后为什么会好听,或者可能不好听,我一直对综合性比较感兴趣。而演奏这方面,我永远觉得有很多人演奏得比我好,哪怕我很勤奋,天天练琴,但是感觉演奏时上场就会怯场,我有这个问题。
《听见》: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教育,对你的音乐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?
林亿:中央音乐学院对我的影响是巨大无比的,这个重要性是没法用文字来表达的。因为学校的那些历史大师级人物,我一直感觉到有压力,就是你站在大师的肩膀上,作为校友,你不能特别不给力,对吧。
学校里有中国的各种音乐精英,演奏、作曲、学术等等,跟他们的接触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,尤其是在演奏方面,我接触到演奏家或者演奏专业的学生,他们的水平非常高,乐器已经成为他们身体的一部分。这也促成了我对声音二次进入非常感兴趣的状态,因为这些优秀的演奏家让我打开脑洞去想象,想还能写出什么新的东西,让他们去表达。
《听见》:如果把你和中央音乐学院的中国同学比较,你认为你们之间的艺术创作上会有什么差异?
林亿:如果我跟一个中国同班同学,同时写一个音乐会的音乐作品或者一个项目,我觉得应该是80%以上挺雷同的, 20%可能是个人怎么去理解某个话题或内容。比如有一次跟一个中国朋友聊到大海,我就跟他说了一大堆不一样地理位置、不一样纬度的海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话,他当时看着我就有点愣住了,说感觉很抽象。
这位同学他跟我解释他出生之后,很晚才见到大海。这让我想到我来到中国,已经很大年纪了才看到下雪,这是一样的体验。我出生在一个四季都是夏天的国家,很多东西中国人觉得没什么稀奇,比如高山峻岭,比如大草原,但我会觉得很震撼。我们觉得应该全世界都是一样的,但其实每个人在很深层次的小细节里是不一样的。

扎根
2018年,林亿在北京组建了家庭。他的另一半,是中国的青年琵琶演奏家孙莹,同样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,正是林亿所说的“演奏上的精英”。他们共同创办了一间音乐公司,在音乐事业上相互配合,一个负责作曲,一个负责演奏,完成了《清泉》《长门怨》《蹁跹》等民乐作品。2020年,他们的小宝贝在北京出生。
《听见》:硕士毕业后,你选择留在中国北京继续自己的音乐事业。这是个新的挑战么?
林亿:我觉得全世界的艺术工作者,不论你放到哪个大城市生存,都是有挑战的。
《听见》:不光是因为自己的外籍身份?
林亿:不会,反倒我觉得非常庆幸,我是选择扎根在北京,在中国来开阔我的事业。因为我觉得中国社会很多层面来说,对于外国人还是包容性很强的,工作起来我的身份不经常被提到。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北京这种一线的工作环境,都是追求效率,你能完成好这份工作,那是最重要的,你是谁,你的肤色我不管。我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,我没觉得受过任何排斥。我天天就是考虑着手上有这个任务,怎么样最大化地把它完成好。我在中国写了几个比较小众的作品,很多中国老百姓跟我说很感动。我真的觉得,或者说让我再次确定了,虽然说起来还很俗气,就是艺术或者音乐真的无边界。


《听见》:为什么没有选择回到新加坡?
林亿: 十年前,我在新加坡一间非常顶尖的学校任教,年纪轻轻当上了音乐系主任,在大家眼里很有成就。当时辞掉工作,全世界都觉得我疯了,在所谓的人生巅峰,为什么要放弃一切。但是我一直看得非常清楚,哪怕有一天新加坡总统给我颁了一个奖(这个荣誉),但是我只能说自己在新加坡做了一些别人觉得有贡献的东西。我会想走出新加坡,我有没有给亚洲、给世界做了什么有贡献的东西。
《听见》:您喜欢现在的事业的状态,生活的状态么?
林亿: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觉得可以更好,或者华人的一个象征性就是永远在追求再上一层。在追求更好的路上,我是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,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我走的路比较弯,比较远,我就会提醒自己其实现在有的已经比之前好太多了。
英语有个词,叫“taking baby steps”,就是像小婴儿一步一步的,所以哪怕你多么艰难,你只要能把一只脚放在另外一只脚的前面,你就是成功了,然后再重复,再把另外一只脚放在前面,然后再重复,这样就够了,不需要你再做更多。